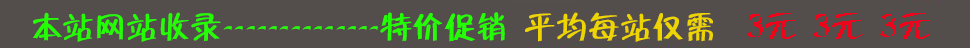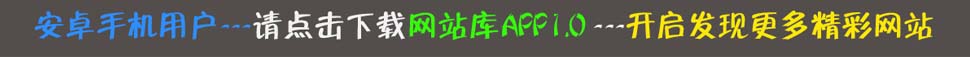這個結論本身價值不大,得出結論的過程更有意思。本文主要就是推導過程,帶上腦子,一起來測算。
需要說明,本文緣起是我最近看到一個非常好玩的問題:谷歌最新財報首次披露 YouTube 和云業務收入,除了官宣數字,我們能否結合其他信息,推導出更多隱含信號?

因為深入研究過 YouTube 和 Spotify,文章見:
字節跳動之意不在社交
Spotify:救命稻草還是行業公敵 | Yourseeker 海外研究
行業復蘇,身陷囚徒困境的網易云音樂們該咋辦?
且之前是谷歌、目前是 Spotify 的 mini 股東,出于好奇,我忍不住來回答這個問題,發現一些數字背后的東西。
以下推導過程,將涉及初中數學,海外頭部音樂流媒體平臺的財務數據、競爭現狀以及部分行業潛規則。
三年前,美國唱片業協會(RIAA)的老板說:
“目前一首歌曲的創作者,在 YouTube 上作品每播放 1000 次,大概可以賺得廣告費 1 美元;而蘋果和 Spotify 等付費服務,每 1000 次播放會向創作者支付 7 美元。”
言下之意很明顯:我們不太喜歡廣告,尤其是通過我們的音樂作品賺的廣告費有點少的視頻平臺——YouTube。
其實美國音樂行業與 YouTube 的關系一直有些微妙。這和早期 YouTube 的崛起有莫大關系。
作為介于互聯網和電視之間的產物,YouTube 從誕生之日起就自帶 UGC 模式加持的雙重特點——內容成本極低、版權保護極差,最早幾年更是內憂外患不斷。
內憂是,YouTube 夾在電視版權方、觀眾和廣告商之間,難以平衡三方關系、明確變現模式;外患則是,UGC 用戶漠視版權,YouTube 難以切實履行電視、廣播、唱片公司要求的監管責任,屢屢引發多方不滿。
后者真正棘手,因為它不只要考量客觀上如何解決,你首先得問問 YouTube,它主觀到底想不想解決。
畢竟就連 YouTube 聯合創始人 Steve Chen 都坦承,最初平臺上大約 80% 的視頻都存在侵權問題。如果它們被刪除,網站流量必然會銳減。
好在 YouTube 最后還是決定刮骨療毒。因為就算利用“安全港”條款可以暫時規避風險,但這種運營方式絕對不具備可持續性。
(注:“安全港”條款規定,網絡服務提供商在收到警告后,如果立即撤下侵權內容,可以不用為用戶的侵權行為負責。)
主觀上既然想解決,那么客觀上如何解決?簡單來說 YouTube 的思路是,自己很難解決,那就賣了,讓別人解決。
因為另一邊有早期投資人紅杉的努力撮合,金主谷歌以當時來看不低的價格收購了 YouTube,風險得以轉移。沒成想,這個 case 后來居然成為谷歌手頭數一數二的投資案例(時至今日和安卓是一個量級)。
所以谷歌入主 YouTube 后做了什么?它主要用兩套方案來解決電視、廣播、唱片公司等版權方的不滿:
其一,短期內支付費用+分享廣告收入,和唱片公司、廣播電視公司達成共識;
其二,長期借助谷歌的技術能力,創建一套名為 Content ID 的系統,監察視頻和音頻版權的不規范使用,保障版權方利益。
這兩步都還算有效,至少穩住了局面,同時還為 YouTube 爭取了發展的黃金時間,由此 YouTube 才逐步成長為全球最大視頻平臺。
但穩住局面并不代表皆大歡喜,尤其是 YouTube 這種用免費廣告替代掉原本收費的行業慣例的做法,動了別人的蛋糕,自然為人不喜。
這是 YouTube 屢遭“嫌棄”的重要背景。
但它顯然也很不忿,雖然很長一段時間被谷歌作為“秘密武器”雪藏,但它還是多次試圖在業務、輿論上搶占高地。2017 年,YouTube 全球音樂業務負責人在某次回懟 Spotify 的場合,側面回應了唱片業協會的指責:
“YouTube 在美國每千次播放帶給創作者的分成其實是 3 美元,比其他所有廣告平臺支付的費用都多。為什么大家不知道?因為 YouTube 是全球性平臺,發展中市場的貢獻太少,所以這個數字被稀釋了。”
聽起來說得過去,但 YouTube 可能覺得還不夠,再加上他們確實不像 Spotify 那樣堅守收費慣例,沒有為音樂行業切實帶來大筆分成,始終難以和主流音樂行業相處融洽。
于是 2018 年 9 月,YouTube 官方又一次聲明:
“過去 12 個月,我們已向音樂版權所有者(唱片公司+創作者)支付了 18 億美元的廣告收入。”
數字挺震撼,但是問題很大。因為后來大家發現,據全球唱片業機構 IFPI 統計,2018 年全球所有視頻流媒體平臺加起來,累計給音樂版權所有者帶來收入只有 9.988 億美元。
所以,YouTube 一家跳出來說給了 18 億美元,別人帶來的其實是負效應?
如果說這次還只是小波折,二者統計口徑差異可能真的太大,那最近再次引發熱議的問題又來了,不久前 YouTube CEO 親自出來給了一個數據:
YouTube 在 2019 全年通過廣告和付費訂閱向音樂版權所有者累計支付了 30 億美元。
這個數字再次引起軒然大波。上次的 18 億大家已經將信將疑,這次的 30 億,可信度有多高?
我們不妨換個角度,來想想如何證明這個數字可信/不可信?以及,如果可信,這將說明什么問題?
鑒于 YouTube 不可能給出相對公允、經審計的各項財務數據,我們只得回過頭來找些可比公司,用可靠數字做橫向比較。
第一家可比公司自然是 Spotify。2019 年財報顯示,它全年收入 67.6 億歐元,合 76.0 億美元。

需要指出,目前主流唱片公司(索尼、環球、華納等)和 Spotify 的合約大概是,后者支付 52% 的收入作為音樂版權使用費,外加 13% 的收入給到創作者。
也就是說,Spotify 總共向音樂版權所有者(唱片公司+創作者)支付約 65% 的收入。
(備注:這個數字和 Spotify 財報里的“收入成本”數字不一樣,因為財報里的“收入成本”還包括信用卡、三方支付費用等。)
2019 年 Spotify 收入的 65%,就是 49.4 億美元,這比 YouTube 聲稱的 30 億高了 20 億。
單純談論收入意義不大,我們加個角度。截至 2019 年底,YouTube 全球月活超過 20 億,而 Spotify 財報里說,自己截至 2019Q4 的月活是 2.71 億。

也就是說, 2019 年,YouTube 月活用戶人均給音樂行業的貢獻是 1.50 美元(30 除以20);而 Spotify 是 18.23 美元(49.4 除以 2.71),二者差距在 10 倍以上。
當然,這個算法有點問題,因為不可能 YouTube 的所有 20 億用戶都享受了音樂服務。
而且 YouTube 是視頻平臺,Spotify 是音樂平臺,比較二者的人均音樂貢獻似乎不夠公平。再加上,二者商業模式有根本的不同,Spotify 顯然占了付費模式的便宜。人均貢獻值高也是正常。
那么我們不妨來看二者和音樂相關的廣告收入。如 YouTube 所說,自己 2019 年向音樂行業支付了 30 億美元廣告收入。
但 Spotify 的 2019 年廣告收入才多少?6.78 億歐元,合 7.34 億美元。
這樣測算,YouTube 月活用戶人均給音樂行業的廣告貢獻是 1.50 美元,而 Spotify 是 2.70 美元(7.34 除以 2.71),總算是相對可比了。
只比較 Spotify 顯然不夠盡興,我們可以拉出第二家可比公司——Apple Music。現在的場面就有些神奇,谷歌旗下視頻網站做音樂,蘋果手機自帶音樂服務,這二者誰強誰弱?
或者換句話說,我們都知道 Spotify 已經坐實全球第一音樂流媒體平臺,YouTube 和 Apple Music,誰會是第二?
以下數據就不像上面所舉的財報數字那么嚴謹了,但參考意義肯定還是很大的。
首先,Apple Music 在 2019 年 6 月宣布,全球訂閱用戶超過 6000 萬,相比 13 個月前的 5000 萬增加了 1000 萬(這些數字均包括蘋果的免費試用版)。
也就是說,每月平均新增 77 萬(1000 除以 13),那換算到 2019 年底,Apple Music 付費用戶應該有 6500 萬(含免費試用版)。
所以,如果 Apple Music 在 2019 年底付費用戶數量達到 6500 萬,且 ARPU 是 5.16 美元,那么 Apple Music 的 2019 年收入就是 40.2 億美元。(ARPU 取下限值,付費用戶數量取上限,也算是一種對沖誤差。)
再按照我們開頭提的,假如蘋果在面對唱片公司時話語權和 Spotify 相當,把 40.2 億美元的 65% 分給音樂版權所有者,那么蘋果 2019 年就需支付 26 億美元;如果退一步,它不如 Spotify 強勢,再分多些,70%,就是 28.1 億美元。
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?別忘了,YouTube 說自己去年累計支付了 30 億美元。
結論呼之欲出:要么 YouTube 粉飾數據,要么它比 Apple Music 還強,從貢獻收入的角度看已經是事實上的全球第二大流媒體音樂平臺。
注:本文部分 Youtube 負責人發言引用自 musicbusinessworldwide 網站,這是一個關注音樂行業挺深的優質平臺。